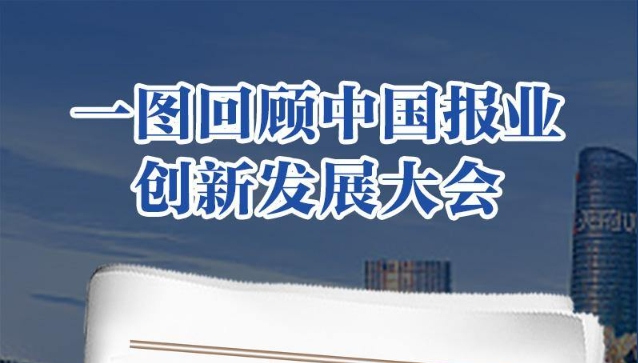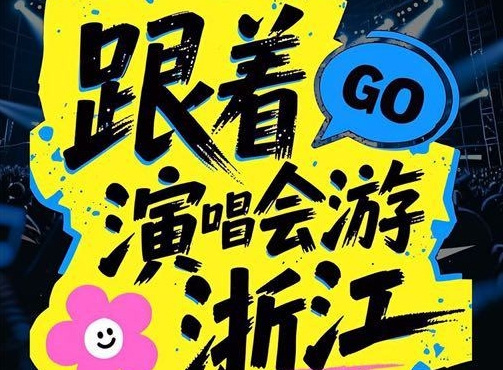高密度人口是浙江改革发展较快的助力。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浙江,贫而不困,透着商业机会和创业活力。浙江宜居空间密度曾居全国各省区首位。1978年,浙江宜居空间每平方公里1348.1人,约是全国平均的2.5倍。2023年是全国平均的3.0倍,居广东之后、列各省区第二。浙江人均耕地近乎全国最少,1978年为0.74亩,只有全国平均1.55亩的47.3%;但浙江耕地复种指数全国最高,1978年为259.0%,比全国平均高70.6%。
浙江农民是最勤劳的农民,即是由上述数据导出、支持,也是关于浙江发展的一个重要判断。1978年,浙江农业人口3322.0万,占全省88.6%。农民必须在较少耕地上投入较多劳动,“一年忙到头”,才能维持全家生计。1978年至1995年,浙江耕地复种指数平均250.6%,全国首位,大大高于全国算术平均的155.6%。
浙江农民的勤劳,是与自然环境长期博弈的结果。具体而言,是适宜气候加持下的人地关系高水平均衡的结果。光热水气同步的气候、滨海和山谷冲积平原为主的肥沃耕地,以及和平时期较快增加的人口所导致的较多劳动投入,不断推高气候、土地和人口三者的均衡关系。在浙江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土地对于劳动投入具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从而在较长时间里,支撑了土地产出与人口的双双持续增长,孕育锤炼了浙江农民的勤劳、精明、务实和开拓,形成了高密度的宜居空间人口。
这一模式在农业社会具有边界制约,但这时迎来了改革开放,甩开了加之于农民身上的束缚。浙江与上海血肉相连,获得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技术、市场、管理等支持;省内在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乡土文化和习俗,成为企业家精神孕育的肥沃土壤;政府较快转型,是浙江发展的又一有力支撑。浙江快速发展的大戏,正是在这一系列积极因素及人口密度助力下,绚烂展开。
何处不效率。高密度人口形成了规模经济的环境本底,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分工对规模的要求,亚当·斯密说:“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但这在浙江基本不是问题。2023年,全省有30个设区市的主城区及县市的每平方公里宜居空间人口高于2000,其人口合计约占全省七成以上。如此多的人口有如此高的密度,创业者能在较小半径内具有足够的销售额,能便利地获取劳动力和原副材料,能较快形成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创业门槛较低,成功概率较高。
运输占企业销售比重较低,因缺少相应数据,以人口普查的交通运输及相关从业人员占比替代。2000年五普,浙江交通运输及相关从业人员占全省非农从业人员5.7%,比全国平均低1.5个点,高于广东、北京,列全国第三。2020年七普,浙江交通运输及相关从业人员占全省非农从业4.6%,比全国低1.7个点,全国首位,比第二的广东低0.5个点。全国快递企业主要发轫于浙江,多半拜人口高密度导致的交通运输高效率所赐。一个相对较小的交通运输业服务于一个相对较大的经济,显著表明浙江经济的交易成本较低。
何处不发展。这也是浙江经济饱受“低小散”“指责”,但发展仍较快的一个奥秘,因为人口密度较高,浙江多数地方均有交易成本较低的特点,可谓“设厂成本处处较低,发展差距点点相近(各地发展较为均衡)——近乎任一区域均有项目布点可行性”。
何处不都市。高密度人口必定形成高密度城市,乡村也具有大都市的生产生活便利。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村村像城,城城像村”说法,是浙江城市化混沌期景象的经典描述。1996年,浙江行政村距本乡镇的距离,2公里以下范围内的人口占38.3%,比全国平均26.6%高11.7个点,系全国各省区首位。浙江不少地方沿交通干线,形成长达数10公里乃至100多公里的城镇绵延带。
政府相对较小。高密度人口带来了政府的规模经济性,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服务于一个相对较大的经济,有利于增强微观活力。因发展较快而大量吸收外来人口,进一步导致“小政府”效应。2020年七普,浙江的政府相关人员占全省从业人员3.0%,比全国平均低1.0个百分点,仅高于广东的2.9%,自低而高排序列全国第二。2023年,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的15.0%,约比全国平均低3.8个点。
人口密度在特定条件下具有转换为动能的较大概率,是理解浙江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浙江城乡一体融合走在全国前列的一个基础条件。当前,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理解省情,活用人口密度优势,有助于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