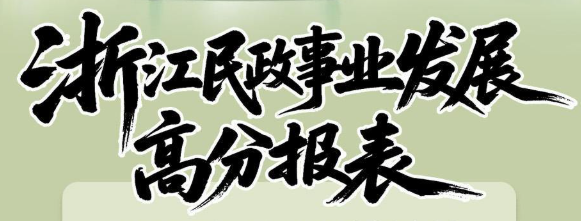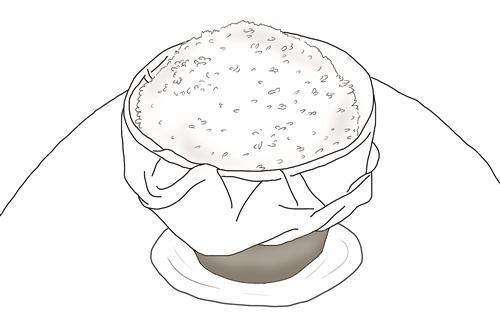
插画 陈静
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上海方言也作了一番精彩的展示。被称作上海传统早餐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粢饭、豆腐浆,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小吃,也是椒江人的传统早餐,虽无四大金刚之名,却有四大金刚之实。
上海话“粢(cī)饭”,等同于椒江话“炊饭”,是将糯米用冷水浸泡,沥干后蒸熟,吃时常捏成饭团,在中间夹油条等。
作为主食的米饭通常是水煮的,而“炊饭”是隔水蒸的。“炊”,现泛指烧火做饭,但最初的含义是蒸。《说文解字》,“炊,爨也”,又说,“爨(cuàn)”字的上部像人双手抱着“甑(zèng)”。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甑”是带孔的蒸饭器具,蒸饭时,在甑底垫上箅(bì)子,然后将米放在箅子上蒸。南唐徐锴《说文系传》:“取其进火谓之爨,取其气上谓之炊。”也认为“炊”是用气蒸。唐慧琳《一切经音义》说得更直接:“炊,蒸也。”宋戴侗《六书故》也有详细说明:“今人以木为甑,如桶而无底,着箅以炊饭。”这些都证明“炊”的本义是“蒸”。
有研究认为,古代做饭的方式中,蒸饭在先,煮饭后起。三国谯周的《古史考》中记载:“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皇帝首创蒸饭,饭是蒸的,粥是煮的。这也可作为“炊”为“蒸”义的旁证。
有个故事叫“炊饭成糜”,说的是,东汉时,太丘长陈寔家里,有客人来拜访,客人十分健谈,陈寔让两个儿子为他蒸饭招待客人。两个儿子放好蒸锅后,躲在一旁偷听,忘了在蒸锅里放蒸屉,结果米直接落锅,煮成了粥。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说》的文本是:“有客诣陈太丘,谈锋甚敏,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饭以延客。二子委甑,窃听客语,炊忘着箅,饭落釜成糜而进。”“炊忘着箅”,指蒸饭时忘了在蒸锅上放蒸屉。
清黄遵宪《日本国志》中说,“(日本)古时亦尝作蒸饭,故釜额上有三横画者,俗谓之饭釜,以存甑形也。以箅着甑底,入米,安釜上,候略熟,沃水再蒸,谓之炊饭。”
“炊”指“蒸”,跟台州方言相合。方言“炊饭”,作名词,字面意思是,用水蒸的饭,特指水蒸的糯米饭。“蒸‘炊饭’”叫“炊炊饭”。椒江话“整个人搭炊炊饭样个”,形容全身闷热难熬。
“蒸馒头”叫“炊馒头”。《水浒传》里武大郎挑卖炊饼,“炊饼”据说就是馒头。宋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宋仁宗皇帝的庙讳是“贞”,“贞”跟“蒸”音近,为了避讳,宫里的人就把蒸饼改称为“炊饼”。可见这个“炊”也是“蒸”的意思。椒江话里带“炊”字的食物还有“炊圆”“炊皮”“炊虾”等等。
电视剧《繁花》中说到的“粢饭”(字幕),上海话读如“次饭”。宁波话、苏州话也这样说。既然“粢饭”就是台州人说的“炊饭”,那么,哪一种写法是正确的呢?
“粢”,本读如“姿势”的“姿”,是一种谷子的名称,泛指谷物,也特指祭祀用的谷物。“粢”,还可读作“糍”,指糍团、糍粑,“麻粢”就是麻糍的另一种写法。从释义来看,“粢饭”跟本字不合。“粢”,大概是民间借用的形声字,取“次”的音,取“米”之义。研究宁波方言的著作《甬言稽诂》也认为,“粢”是“稻饼(糍团)”,并非散粒的饭,因此,“粢饭”的写法不对。作者认为,糯米有黏性,“黐(音痴)”有“黏”的意思,所以他写作“黐饭”。
我们知道,椒江话里,煮的糯米饭只叫“糯米饭”,不叫“炊饭”,蒸的糯米饭才叫“炊饭”。当下宁波话叫法,有同样的区别,蒸熟的糯米饭才叫“粢饭”。在笔者看来,记作“黐饭”,着眼点只在黏性,无法分辨蒸和煮两种不同的烹饪方法,所以,记作“黐饭”也不妥。
从读音来看,“粢饭”和“炊饭”在上海话老派方言里读音相同(见陶寰、高昕撰《上海老派方言同音字汇》)。苏州话和宁波话,“粢饭”的“粢”,除了读作“次”,还读如椒江话的“炊”。换句话说,若是记作“炊饭”,在椒江方言中可通,在上海、苏州、宁波方言中,至少在老派读音中,也没有违和感,而“粢饭”,不仅义不合,读音跟椒江话也有别。因此“粢饭”不是本字。本字大概就是“炊饭”。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粢饭”,并模仿上海等地的方言,为“粢”造了一个新读音“cī”,这大概是由于“粢饭”使用面广、影响力大的缘故。
把蒸叫做“炊”的,除了江浙一带方言,还有粤语、闽语等。如福州、厦门有“炊饭”,广东东莞说“炊馒头”,客家话、福建话有“炊床(蒸笼)”。
综上所述,台州方言“炊饭”的本字应该是“炊饭”,《繁花》中见到的上海方言“粢饭”,本字应该也是“炊饭”。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