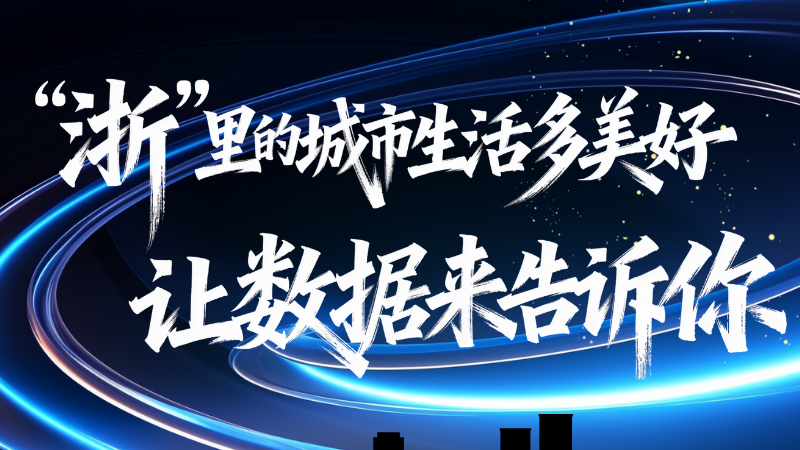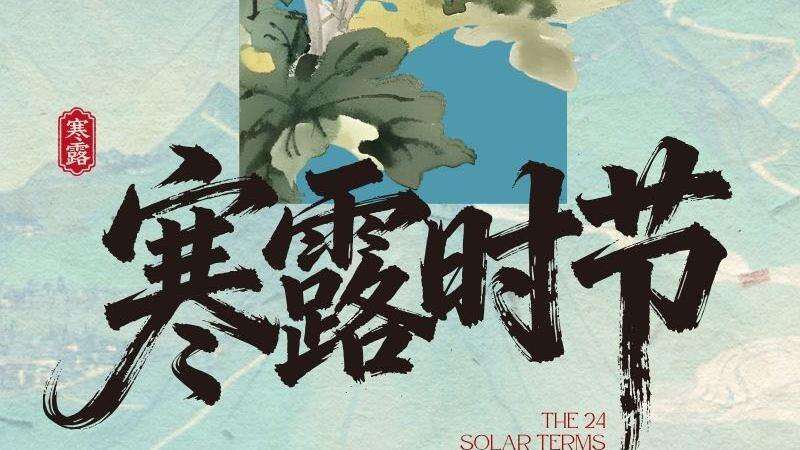10月下旬,余姚市河姆渡镇稻浪翻滚,晚稻迎来收割的季节。
7000多年前,在同一片土地上,一批学会栽培水稻的先民,或许也会抱着期待的心情,等待丰收时节的到来。
走进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展厅里的炭化稻米显得有些不起眼。它们又黑又小,被装在玻璃皿里,只有通过上方的放大镜仔细观察,才能清晰地看清其真容。可正是这“小东西”,在中国稻作农业早期发展阶段具有独特价值。
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召集农民扩建姚江排灌站机房。在施工过程中,农民发现不少陶片、骨头。由此,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横空出世。
考古现场,在黑褐色的基坑中,一堆堆金灿灿的稻谷令人啧啧称奇。通过碳-14测定,这些炭化稻谷距今约7000年。
在宁波考古70年之际,记者会同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雷少,一起探索河姆渡稻作文化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河姆渡遗址所在区域地势低洼,水起到了有效的隔氧效果,各种有机物质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因此,相比于同时期其他遗址,其稻谷堆积数量之多、保存程度之完好,极为罕见。”雷少说。
另一方面,以骨耜为代表的大量农具,包括骨镰、木杵、点种棒等的发现,充分说明当时的农业早已脱离火耕,发展到了耜种的阶段。
由此,呈现了一幅生动独特的远古江南生活图景——
先民选择在湖泊河流附近的湿地开垦稻田,已初步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方法,过着日出而作,兼营渔猎采集的田园定居生活。他们使用骨耜翻耕农田,再用骨镰进行收割,还会用木杵与臼进行稻谷脱壳,并用陶釜进行烹煮。
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是栽培稻起源地的观点,首次实证了稻作农业“中国起源说”,成为我国稻作农业起源考古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
稻作文化的源流,不止于河姆渡遗址。近年来,河姆渡遗址周边陆续发现多处与之内涵相同的遗址,使得中国稻作农业的形成过程不断清晰。
距离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7公里处,是与其文化内涵基本一致的田螺山遗址。这里也发现了包括稻谷、稻米在内的大量水稻遗存。同时,田螺山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橡子,其在营养成分、收获季节、食用方式、储藏方式等方面与稻谷基本相同。
根据量化分析,水稻是当时人们最重要的食物资源,但橡子、菱角、芡实等也是不可或缺的食物。这说明在河姆渡文化早期,稻作生产力水平较低,还需要通过采集、狩猎补充生活资料。
与河姆渡文化早期几乎同时,位于环太湖平原地带的马家浜文化也进入稻作生产阶段。
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两种文化的稻田形态。马家浜文化的水稻种植多以小块圆形浅坑为主,规模化特征不突出;河姆渡文化的稻田常分布在山体之间的山岙区域,形成了更具规模化的种植格局。
2020年,在距田螺山遗址约400米的位置,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施岙遗址。其中,古稻田遗存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包括史前三个时期的大面积的规整块状稻田,从河姆渡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晚期。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序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古稻田。
施岙遗址古稻田刷新了考古工作者对史前稻作农业的认知。这里的良渚文化晚期稻田系统由“井”字形路网和灌溉系统组成,是稻作农业考古的新突破。这一发现证明,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是养活众多人口的主要食物来源。
仓廪实而知礼节。从此,一份“稻情”,代代相传。几千年来,水稻种植成为人们的主要口粮来源,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坚实基础。
21世纪的宁波站在7000年稻作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大探索和创新:2000年,杂交粳稻“甬优1号”诞生,当年就在全省推广种植20万亩;去年11月,连作晚稻“甬优1540”攻关田实现最高亩产832.69公斤、百亩方平均亩产827.26公斤,加上之前早稻的产量,成功打破全省双季稻总亩产纪录。
7000年沧桑,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于稻作文明而言,却是从“驯化一粒米”到“种出一片田”的漫长蝶变。
这片土地,始终在四季轮回里,书写着丰收的故事。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