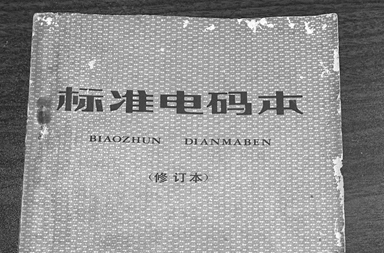《标准电码本》和内页
当你一言不合拿起手机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时,是否能够想象40多年前,人们遇到急事需要反复斟酌盘算文字,仅仅只是为了发一封电报?
上世纪80年代,电报作为人们传递消息的重要方式,可谓“红透半边天”。以1988年为例,浙江省全年的电报业务量就有2012.3万份,杭州有194.85万份。
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这种“古老”的通讯方式和老百姓的生活渐行渐远。此前,中国电信公司发出公告,今年5月1日起,将全面停止杭州的电报服务。
百年电报走到终章,这“滴答”声曾奏响一代人的悲喜,是盼子早日归家的急切,是分享婴儿第一声啼哭的喜悦,是告别、跨越,更是当代人回望历史的钥匙……
老一辈营报员还原时光碎片
一台小小的电报机,却能敲击出万千字符。尽管目前杭州依然能够办理电报业务,遗憾的是,这些电文,并非由传统电报机发出,而是在电脑上输入文字、打印之后再寄出。
幸运的是,几经辗转,我们找到了老一辈营报员陈钟英。她给我们还原了电报鼎盛时期的一些时光碎片。
很多和她一样的老杭州人对电报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那个电话、网络没有兴起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信件,而信寄到外地少则一两天,多则一周半月,如果发往交通更为闭塞的地区,时效更没保障。一旦有要紧事,电报就成了彼此间最快捷的沟通渠道。电报,可以无视距离,跨越山海,把想说的话第一时间送达。
发电报需要去营业厅办理。先填一张电报纸,写上收报人姓名、地址及电报内容。价格按照字数计算,一个格子三分钱,特殊处理的加急件,一个格子六分钱,除了正文内容,收件人地址、姓名等都要算钱。
在那个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的年代,发一封电报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所以,人们每次动笔写报文前,总要逐字斟酌,尽量简明扼要,绝不多写一个字。
为了早一点把电报送达,送报员每天骑着自行车,挎上邮递员包,风风火火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但有意思的是,街里街坊对于电报的感情是很微妙的,带着一丝忐忑和期待。
陈钟英解释,这是因为,那时电文的内容,不是大喜就是大悲,收件的户主在听到消息后,总会不自觉地紧张,双手颤巍巍地接过来,还没拆开就开始担心,尤其害怕收到类似亲属发来的“病危速归”的电报。
“电报早已是我的另一个‘孩子’”
今年70多岁的陈钟英,年轻时是收发电报的一把好手。她的工作,简单地讲,就是把大家想说的话,转成电码发出去。
“熟记电报电码就是营报员的立身之本。”陈钟英回忆,每一个汉字都有对应的4位数字,打错一个,整句话的意思有可能就变了,因此那个时候的电信业对于差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错一个字是要扣钱的,如果在电文发出之后被发现了错误,罚款金额会更高。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独生子女’打成了‘毒生子女’,幸亏师傅仔细,给检查出来了,少交了一次罚款。”
聊到曾经热火朝天的画面,陈钟英说,每天屁股基本跟粘在凳子上了一样,从坐下的那一刻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敲键盘,“报务室里来发电报的市民一波接着一波,基本不带停的,同事之间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全是滴滴答的响声。”
长期高效的工作,让她练就了肌肉记忆,一本《标准电码本》共计14000余字,以前常用的3000多字对应的电码烂熟于心。即使退休20多年后,还能精准报出许多汉字对应的4位电码。比如,见面后没多久,陈钟英随口给了我一个惊喜,“你姓周,在电码里的代号应该是‘洞拐幺勾’(0719);小王的王,应该‘三拐六勾’(3769)。怎么样,我这记忆力还可以吧!”
在大家惊叹的目光中,陈钟英摆摆手,不以为意,“以前拿来的电文,基本上扫一眼就能转换,1分钟打出100多组字符,每天三五百封电报不在话下。不过后来,随着电话的日渐普及,发电报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虽然退休多年,回忆起当年在报房的点滴,陈钟英便神采奕奕,尽兴之处,还会手舞足蹈地比划。
得知杭州电报业务将在5月1日关停的消息,她一时间感慨万千,“虽说电报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但是在我的心里,‘她’就是我的另一个‘孩子’,只是长大毕业,离开我身边外出去闯荡了而已。”
停顿了一下,陈钟英又说:“电报不是被淘汰,而是完成了使命。”
有人感受“慢时光”,有人不舍告别
听完陈钟英讲述的故事,我们想去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看。
没想到的是,出发前,办公室的同事们率先炸了锅。作为90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于电报的印象,基本停留在影视资料,“现在还有电报”“电报是怎么发送的”“多久能收到”……
带着这么多人的好奇和疑问,前天(3日)上午11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地铁武林广场E出口附近的中国电信营业厅。一进门,就注意到了醒目的告示牌,上面用蓝色大字写着:杭州电信电报业务退市公告。
在南京读书的大三学生小田大前天(2日)早上和同学从学校出发,下了高铁列车,就直奔武林广场的电信营业厅。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手里的电文有些“特殊”,上面不是中文,而是密密麻麻排列成一串又一串的数字。
小田有一本《标准电码本》,是他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的。办完手续后,他还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收据留存纪念。
2007年出生的姑娘小郑正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对于怎么收发电报,她充满了好奇,“和我的朋友约定好了,等她收到之后再转寄给我,这是一种仪式感,也是我们感受慢时光的一个机会。”
当天,前往二楼办理电报业务的市民中,除了像小田、小郑这样感受“慢时光”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不舍告别的怀旧者。
市民张女士说是在网上看到消息的,“因为家住附近,经常会到这个营业厅来办理业务,可以说见证了电报的兴衰,以前家里老人去世就是用电报通知亲戚朋友的,虽然它快要退市了,但是我对它的感情还在。”
一上午,营业厅电报接收室的桌子上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沓电文。工作人员说,这两天每天都能收到200多份,久违地迎来了“高光时刻”。
这穿越百年的“滴答”声终将消散,那些由电码带来的悲欢,早已在数字洪流中沉淀为文明的琥珀,并提醒着我们:技术可以迭代,但连接的温度永不褪色。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