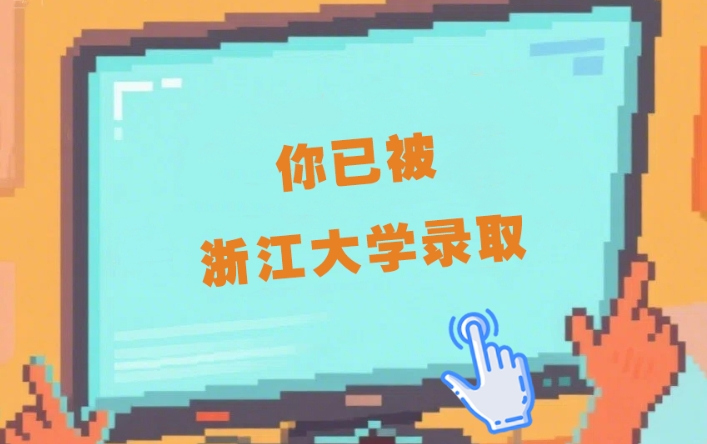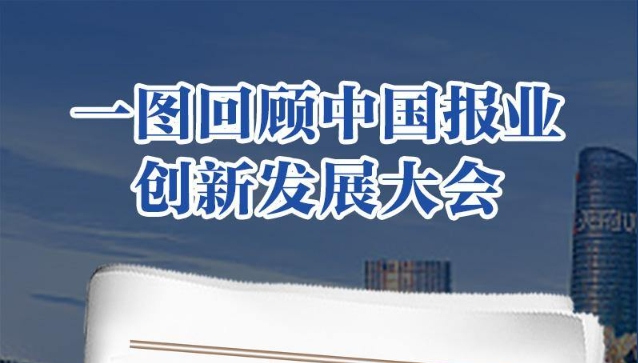1942年10月2日早上,舟山外海的海面上,日本货轮“里斯本丸”号被美军潜艇击中,1800多名英军战俘破舱逃生,在海上奄奄一息。史书记到此往往戛然而止,仿佛剩下的只是冰冷的海水和统计数字。世界史的大叙事正忙于勾勒斯大林格勒的“钢铁洪流”与中途岛的海空对决,舟山群岛最外缘的东极岛只是地图上一粒可被忽略的微斑。《东极岛》创作团队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把摄影机对准了这粒微斑——或者说,对准了那些在史书上连脚注都没留下的渔民。影片的野心不在重现战役,而在追问,当宏大叙事退场,艺术如何用“人”字的偏旁部首,重写那段海上的人性史诗?
阿赑的“三次呼吸”
影片初期,弟弟阿荡(吴磊饰演)欲救回落水英国战俘纽曼时,哥哥阿赑(朱一龙饰演)坚决不同意,为人物成长预留了空间。而当日本人上岛,以村民们私藏英国战俘为由当众杀害吴老大等村民,并掳走阿荡等扣为人质时,阿赑拯救至亲的人性底层动机与阿荡在船上救人的行为,螺旋上升为一种更强烈且朴素的救人愿望。阿赑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忍行径,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他不再是那个只想自保的普通渔民,而化身为勇敢的抗争者。
在哨所一战中,阿赑孤身一人,手持利刃,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朱一龙通过精湛的演技,将阿赑的愤怒、仇恨与勇敢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痛失胞弟且得知日军准备屠村的消息后,退无可退的他成了这场大营救的先锋。这次“反杀”不再是动作片式的爽点,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代偿”。
影片用三次“呼吸”标记阿赑——不是台词,而是肉眼可见的胸腔起伏。第一次,他在海底捞鲍鱼,气泡成串,节奏轻快,那是一个在驻岛日军看守下的“顺民”青年。第二次,失去养父和弟弟的他独自潜到沉船底,镜头静止,气泡骤停;当他猛地抬头,一串浑浊的气泡冲出,仿佛把悲伤吐进海里。第三次,当他将阿花抛来的锚钩接上英军抛来的缆绳时,最后一丝气力用尽,深呼吸成了生命的绝响,他也如鲸落般沉入海底。三次呼吸,把“怕死—求生—忘我”的人物成长写得极富节奏感,使观众的心跳跟随银幕上的人物命运起伏。
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的奋起反抗,阿赑这个人物展现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蜕变。其成长历程不仅是个人的觉醒,更是整个东极岛渔民群体觉醒的缩影。他让我们看到,在面对邪恶与压迫时,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勇气与力量。
外乡人的坚持与反抗
影片主要人物其实都是外乡人。阿荡,是跟阿赑一起被吴老大从海上捡来的孩子,与阿赑构成一体两面。阿荡性格活泼开朗,但眼神中透着灵动与纯真。正是这份纯真,使得他在影片中从头至尾贯穿着一种渔民对祖训的坚持——落水的人一定要救。
倪妮饰演的阿花,是被吴老大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她砸开了被父亲吴老大封存的宗祠之墙,以贯彻祖训的方式说服岛上渔民出海救人。阿花展现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独特价值与力量。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女性并非战争的旁观者,而是勇敢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陈先生作为岛上唯一的教书先生,身上散发着与传统教书先生身上的书卷气格格不入的痞气。平日里他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将“怒发冲冠”的种子播撒在东极岛的土地上。他深知在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下,民族气节对于一个岛屿的意义。他虽然当过逃兵,但坚守着“逃兵也是兵”的信念,以奋不顾身的态度和巨大的悲剧力量,实现了“精忠报国”的承诺。
保长李元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在日军的压迫下,他为保全岛上居民的性命,起初选择妥协与退让。然而,当他看到同胞因保护战俘而被日军杀害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意识到,一味的妥协并不能换来和平与安宁,只会让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因此,并非渔民出身的他,面对漩涡的纵身一跃方能表现出巨大的人格力量。这一角色展现了一个小人物的成长与蜕变,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复杂的环境中,人性中的正义与良知也终究会战胜怯懦与自私。
影片采用渔民兄弟与英军战俘“双主线并行”的形式。“里斯本丸”号上的英军战俘,是影片中一组特殊的角色群像。他们曾是驰骋战场的士兵,却沦为阶下囚。当货轮被击中,他们坠入冰冷的海水,更陷入生死绝境。语言的隔阂与文化的差异让他们难以敞开心扉,但当他们看到阿赑、阿荡兄弟奋不顾身地帮助自己时,冰封的内心逐渐融化。军官纽曼与少年阿荡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用简单的手势和眼神传递着感激与信任,在危难时刻甚至挺身而出保护村民,最终被日本军官残忍地杀害。英军战俘从最初的被动接受救援,到后来主动掀翻日本巡逻艇的转变,展现出超越国界的人性之美。
水下戏是伦理姿态
影片拒绝用配乐铺陈情绪,而让风声承担了最重要的修辞作用。起初,风掠过阿赑木船的桅杆,发出木质的呜咽;之后,风卷着海水砸在“里斯本丸”号倾斜的甲板上,像急促的鼓点,敲响了对英军战俘生命的倒计时;结尾,风停了,海面平滑如镜,幸存的英军战俘在中国渔民的船上呆滞地看着海面上漂浮着自己同胞的尸体。而这给观众带来的却是更深的颤栗——原来寂静也可以是一种暴烈。此时,风已经不是背景音,而是一个“角色”。
浪的三次变形,也参与了电影的起承转合。起初,浪是柔软的,轻轻托起阿赑的木船,像母亲的手;随着营救剧情的推进,浪变成“墙”,船被抛上浪尖又坠入谷底,观众在座椅里仿佛能感到失重;最后,浪慢慢退去,海面化成了镜子,倒映出满船沉默的人影,死亡与得救同时发生。
影片接近40%的水下戏份被反复提及,其真正价值不只是技术炫耀,而是一种伦理姿态。当镜头沉入水下,战争的噪音被海水隔绝,观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与气泡声——那是一种被强行植入的“共溺水”体验。8分钟一镜到底的水下搏斗,让观众与战俘一起经历缺氧、寒冷与失重,从而把“救援”从道德层面的赞美,推向生理层面的感同身受。
银幕上,83年前的渔民用木船划出了一道“主动叙事”的弧线。更深一层,它满足了Z世代对“历史参与感”的需求。与传统主旋律作品的“仰视”视角不同,影片中的渔民有恐惧、有算计、有私心,这种“不完美的正义”恰恰让年轻观众找到代入缝隙——原来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普通人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在“躺平”与“内卷”并存的当下,这种叙事提供了一种温和的激励——你不必成为钢铁侠,只需在关键时刻把船划出去。
《东极岛》最终留在观众视网膜上的,不是沉船,而是一艘载着阿花的孤独小木船。影片此时用极慢的镜头运动、极简的构图、极阔的留白,把“平民史诗”写成一首长诗。当灯光亮起,我们走出影院,脚下是城市的柏油路,耳边却仿佛仍有木桨划水的声音——那是电影偷偷递给每个人的、下一次出海的暗号。
(作者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珠江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