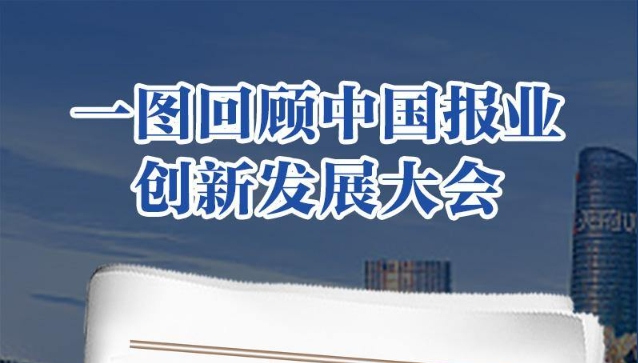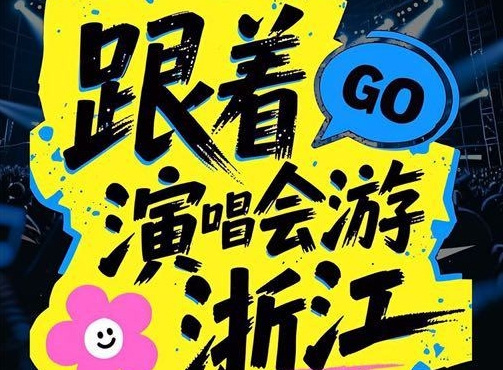疑问
老年助餐需求越来越大,旨在解决老人“吃饭难”的城乡社区食堂,为何依然难以走出经营困境?
调查
餐饮行业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城市社区食堂的普惠性与营利性如何兼顾?
乡村社区食堂大多依赖村集体经济兜底,“自我造血”能力如何?
城市老人用餐有何特点,社区食堂能否满足需求?乡村许多老人不愿意去食堂就餐,原因何在?
思考
破解城乡社区食堂当前困局,不仅要致力拓展消费群体、丰富服务主体,还要改进与创新运营模式,拿出精细的绣花功夫。
城乡社区食堂的政策红利,并非全民普惠,补助导向应该更精准,政策扶持应该更高效。
城乡社区食堂的建设运行,不是一时之计,也不仅仅是政府、社区的事,必须健全形成社会各方广泛参与、资源力量充分统筹的共建共享长效机制。
浙江在线7月15日讯(记者 张蓉 张银燕 梅玲玲 陈醉)一菜一汤之中,自有一番幸福滋味。
以老年食堂为代表,旨在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的浙江城乡老年助餐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早在2018年,助餐配送餐服务就被列为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全省拥有老年食堂6800多个、助餐点5000多个。

老人在杭州市翠苑一区食堂“翠食坊”就餐。 记者 张蓉 摄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浙江各地很多老年食堂纷纷转型为面向全年龄段居民开放的社区食堂。但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社区食堂经营主体收支难平衡、服务对象需求难满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浙江城乡社区食堂的运营现状如何?又该如何兼顾公益与效益,成为长久飘香的“幸福食堂”?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深入浙江各地调研,探寻城乡社区食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普惠与营利的平衡
红烧鱼块、宫保鸡丁、莴笋山药……20道菜铺满餐台,老人们排起长队。上午10时30分,杭州市翠苑一区食堂“翠食坊”进入用餐高峰,近300平方米的餐厅内几乎座无虚席。
这里供应一日三餐,荤菜定价12元至18元,素菜定价6元至15元,对老人给予五到七折优惠,并设有“15元两荤一素”等长者套餐,平均每天有500多人光顾。
临近中午12时,老人就餐高峰结束,更多的面孔出现了:来不及烧饭的宝妈带着孩子来了,旁边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结伴而来,还有匆匆赶来的保安、骑手……
“翠食坊”是浙江第一家老年食堂,于2003年开业。如今,杭州拥有800多家老年食堂(含助餐点),像“翠食坊”这样已转型社区食堂的,约占80%。
食堂转型,是社会需求使然,也是自身生存的选择。其背后,还依然隐藏着老年食堂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伴随的头号难题:“自我造血”难,即普惠性与营利性难以兼顾。
“转型为社区食堂,消费群体扩大了,但普惠性没有变,老人仍然是主要让利服务对象。”负责运营的绿城物业集团杭州餐饮管理分公司项目经理胡琪说,现在餐饮行业经营成本越来越高,“翠食坊”平均每月要为老人让利约5.79万元,好在还有占比45%左右的其他客流填补,才勉强实现微盈利。
胡琪负责的另一家社区食堂则处于月均亏损一两万元的窘境:因餐台位置有限,只能提供6荤6素,菜品少,每日客流仅百人左右,其中老年人之外的客流约占三成,“尽管有政府补助,也无法填补优惠让利和各项成本支出。”
这一窘境,在乡村社区食堂同样常见。
调查发现,各地乡村社区食堂大多依赖村集体经济兜底,“自我造血”能力先天不足,一旦经费保障出现问题,就难以为继。
温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负责人算过一笔账:以一家每天服务40人的食堂为例,一年村集体经济补助经费至少10万元,但在温州市3600多个村社中,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过50万元的仅一半左右,“维持食堂正常运营,对村集体经济着实是不小的负担。”
记者曾走访一地某村,食堂本通过社会筹资、政府补贴、村集体经济兜底,让老人月付200元,一天享受两餐。后因政策不允许村集体经济直接投入兜底,食堂经营困难,只能一关了之。
与收支难平衡同样尴尬的,则是另一个老大难:难以满足老人的就餐需求。
对城市老人来说,市区餐饮业高度发达,可选择空间大,而社区食堂很难满足他们对口味、花样的多元化需求。
在杭州市中心一老旧小区,常住老人1800多位,平均每天到社区食堂就餐的老人仅七八十人。“食堂就这么大,菜品也很少。”83岁的独居老人曹立章说,他每周只去一次社区食堂,平时更多时候点外卖,或到附近餐馆就餐。
对农村老人来说,不愿去的理由则很简单:或不方便就餐,或不舍得多花钱。
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江山市廿八都镇林丰村,有110位常住老人。该村食堂内摆放着3张桌子,正午时分,仅6位老人用餐。从2023年营业以来,这里每天最多只有16位老人用餐。
“三菜一汤只要3至5元,但很多老人生活节俭,还是舍不得多花钱。同时,从最远的自然村到食堂要步行约40分钟,老人不方便来,送餐又要增加成本。”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妙花这样解释。
记者调研发现,农村尤其是山区乡村食堂,像林丰村这样就餐人数偏少的现象相当普遍,“自我造血”更是无从谈起。如江山市4个偏远山区乡镇,常住老人5000多人,但运营的16家食堂中,有7家日均就餐老人数量低于10人。
找准供需最优解
对文成县巨屿镇孔龙村来说,开办老年食堂也曾是怎么算都算不赢的账,如今却拥有与城市社区食堂相媲美的“高配版”:面积达400平方米、摆放着25张桌子的餐厅,能容纳100多人同时就座,每餐有20多道菜品可供选择……开办两年来,食堂不仅稳定运转,还为村集体增收10多万元。
这得益于该村对食堂消费群体的挖掘——向周边企业敞开大门。孔龙村紧挨着巨屿镇工业园区,园区内有18家规上企业。食堂开业前,孔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长兴拿着菜单跑园区,一举说服3家企业与食堂签订合作协议。
客源增多,收入增多;经费更有保障,菜品也就更丰富,从而吸引更多客源……该村食堂迅速进入良性循环,目前每天接待人数稳定在两三百。
像孔龙村食堂、“翠食坊”一样,拓展潜在的消费群体,是城乡社区食堂破解当前困局的常见对策。
事实上,开办社区食堂未必都要个个“另起炉灶”。探索与周边企业或单位食堂、餐饮店铺等合作共建,撬动更多服务主体参与,也是一种解题思路。
杭州市西湖区蝶园社区有2个居民小区、9个商业园区,60岁以上常住老人逾千人,老龄化程度高,但附近没有建造食堂的场地,社区也没有做餐饮的团队和经验。
食堂怎么开?开在哪里?如何运营?蝶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江佩告诉记者,反复权衡之下,社区决定创新思路,与拥有成熟餐饮运营团队和经验的中宙控股集团合作,就近将其旗下一家益尚餐厅改造成社区食堂,“没想到一举‘火’了。”
据餐厅负责人介绍,面积达500平方米的餐厅内,设有老年自助餐专线、小碗菜窗口、小炒菜窗口等特色项目,日均客流量多达七八百人。
如果说拓展消费群体、丰富服务主体,要受到诸多外在因素制约,那么,城乡社区食堂运营模式的改进与创新,无疑更具灵活性和可复制性。
目前,浙江城乡社区食堂的运营模式主要有三种:单独运作;社会餐饮企业挂牌参与;中心食堂集中烧制,配送到助餐点。
为解决地广人稀的山区留守老人就餐需求,遂昌县联合5家餐饮企业建设中央厨房,开通26条助餐路线,配备26辆助餐车,实行“统一采购、统一烹饪、统一派送”,既保障了质量、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经营成本、减少了消费支出。目前,全县已实现预订式送餐乡镇(街道)全覆盖、村(社)覆盖率86%,使2000余位山区老人吃上了美味实惠的“暖心饭”。
很多时候,运营模式创新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大动作,更需要因地制宜,拿出精细的“绣花功夫”,找到供需“最优解”。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临近饭点,很多老人手拎一袋袋自家种植的各种蔬菜走进社区食堂,按市场价兑换成餐券。“‘以菜换餐’切中了乡村老人的节俭心理,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又让他们吃得新鲜、放心。”东吴镇副镇长郑兰说,模式创新后,用餐人数翻了三倍。
位于杭州市上城区青年路的“青邻”食堂,除了提供丰盛的早餐,中午还创新售卖小碗菜,为老人提供口味清淡的优惠餐食;到了晚上,则又切换为选择更丰富的点菜模式。每天一到饭点,经常座无虚席。
廓清两个误区
一粥一饭,三餐四季,是百姓生活的基石。
这些年,为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发展。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部门还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完善老年食堂、老年餐桌、老年助餐点等老年助餐服务设施配置,优化功能布局。
尽管现在很多城乡社区食堂的叫法不一,但其初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保障老年人的普惠性就餐权益,服务重点为“不能烧、不敢烧、不会烧”的老年人。
但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少数地方对城乡社区食堂建设,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一惠民之举的健康长远发展,亟须廓清。
一方面,城乡社区食堂的政策红利,并非全民普惠,补助导向应该更精准,政策扶持应该更高效。
对于服务对象,补助不能“一刀切”,需优先保障高龄、独居、失能失智等老年群体,真正让刚需老人率先享受福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薛在兴建议,社区食堂应建立基于城乡差异、健康状况、年龄分层的阶梯式定价模型。比如,在乡村实施“年龄+收入”双维度补贴机制,让80岁以上老人及特殊困难群体享受更高补贴;在城市基于老人的健康评估等级,实行差异化补贴。
结合精准评估和自主申报,让食堂的公益性更多地向刚需老人倾斜,也正是浙江助餐服务发展的方向。
对于经营主体,扶持不能一味“输血”,需想方设法引导其提升“自我造血”能力。
目前,大部分城乡社区食堂的运转,都离不开财政支持,有的是减免房租,有的是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或者定期发放运营补贴。
“政府补贴保障了基本服务的提供,但长期依赖财政‘输血’,容易削弱助餐机构的独立运营能力,抑制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迭代。”薛在兴建议,应建立绩效导向的分级补贴体系,将服务质量、技术创新等纳入考核,对考核优秀的机构给予额外奖励;建立补贴退出过渡机制,对连续3年经营不善的机构,降低补贴比例。
另一方面,城乡社区食堂的建设运行,不是一时之计,也不仅仅是政府、社区的事,而是长久之策,是全社会的事,必须健全形成社会各方广泛参与、资源力量充分统筹的共建共享长效机制。
对此,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宝胜认为,城乡社区食堂从规划建设开始就要避免盲目攀比、大干快上,应结合实际,从长计议、科学决策,通过前期调研与数据分析,摸清区域人流状况、社区家庭结构、人群意愿与生活习惯等,对布局位置、数量、运营模式等进行统筹规划。
长期关注社区食堂发展的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莫艳清则表示,社区食堂建设切忌财政或集体经济包揽,应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力量广泛与深度参与,真正体现共建共享。
调研中,多地探索受到专家学者的推许。
通过集聚社会资源、动员公益力量,诸暨市探索出一套“爱心食堂”长效机制:党员带头捐、群众互助捐、老乡爱心捐,总规模超2亿元的村级关爱基金给足了食堂“安全感”;爱心厨师、爱心帮工、爱心送餐员等5000多名志愿者的参与帮助,有效减轻了食堂的运营压力。
依托邻里互助网,磐安县、景宁县等地倡导推行“加双筷子”行动,鼓励条件允许且有意愿的农户,就近就便解决老人的“吃饭难”。
一箪食,一瓢饮,小食堂背后,自有大民生。回应老人所需,办好社区食堂,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如何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每个人。
希望当老人们端起一碗碗可口、实惠、充满烟火气的热饭时,感受到的不仅是饱腹的满足,更是“老有所养”的幸福“食”光。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