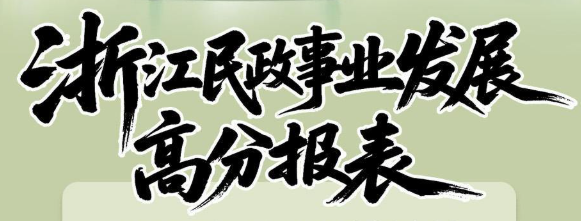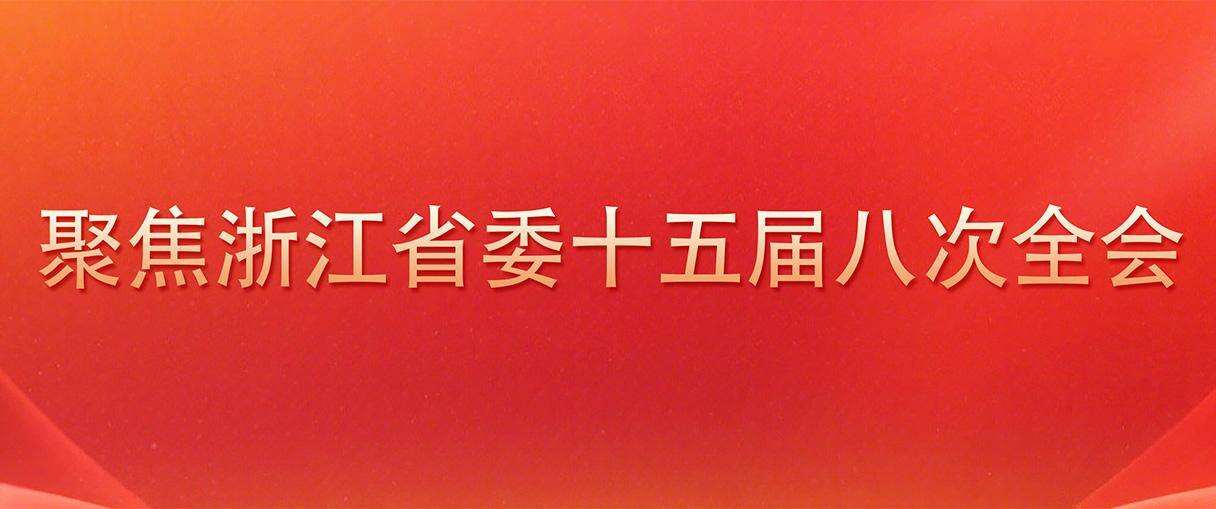浙江在线11月26日讯(记者 林晓晖 严粒粒 通讯员 李文芳 乐小舟)11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25年院士增选结果,我国微创外科领军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喜讯不胫而走。然而,在杭州的浙大邵逸夫医院,波澜的中心却异常平静。蔡秀军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变化,次日清晨7时,他准时出现在医院——前一天因公务推迟的门诊,他及时补上,问诊、查体,耐心听患者说病情……
蔡秀军还会在手术间隙走进年轻医生的操作间,为他们解答那些最复杂、最棘手的技术难题,就像他从医40多年里的每一个工作日一样。
此刻,我们走近这位新晋院士,不仅是为回顾一位医者四十载的执着求索,更是为了循着他的目光与足迹,去探寻一个根本命题:究竟,什么是“好的医疗”?

蔡秀军在查房时与患者交流。 受访者供图
叩问一道伤疤,体察患者最深层的痛苦
在蔡秀军身上,“微创”不仅是一个技术标签,更是一种医疗的哲学。
翻开他的履历——发明国际上第一种专门用于腹腔镜肝切除的手术器械、首创完全腹腔镜绕肝带法二步肝切除术、完成国内第一例完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这些创新都有一个共同的“圆心”:如何用更小创伤、更优技术、更智能的方法治好病人。
在浙大邵逸夫医院普外科,这个国内肝胆疾病微创治疗的王牌科室,每年开展的近万台手术中,九成以上可用微创完成。而从医40年的蔡秀军,是这个团队的领路人。
说起外科手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怕——怕疼、怕留疤,更怕手术后还得再挨一刀。

蔡秀军(中)在手术中。 受访者供图
“外科医生的每一刀,都关系到病人能不能少受一点罪,能不能保住一条命。”这句话,源于蔡秀军早年的深刻体验。
上世纪90年代,还是实习医生的蔡秀军站在手术台旁,目睹传统开腹切肝手术在患者身上留下的“蜈蚣疤”——那道从胸口延伸到腹部的巨大疤痕,不仅刻在肉体上,更刻在患者的生命记忆里。与此同时,新兴的腹腔镜技术因肝脏血管密布、缺乏专用器械而举步维艰。
“越难,越要去试!”在导师、中国外科泰斗彭淑牖的鼓励下,蔡秀军开始了近3年的“死磕”。白天完成手术后,夜晚他埋首图纸,反复修改设计,研发适配肝胆领域腹腔镜手术的器械。
1998年8月19日,改写中国肝脏外科历史的一天。
蔡秀军手握自主研发的“多功能手术解剖器”,在患者腹部仅开几个“钥匙孔”大小的切口,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腹腔镜下右半肝切除术。过去需要四五把器械轮流操作的手术,现在一把器械就能完成;出血量从往常的数百毫升降至百毫升内;手术时间从数小时缩短到几十分钟。
这种价格低廉、性能卓越的“中国造”器械,打破了国外垄断,应用于全球300多家医疗机构。他创立的“腹腔镜刮吸解剖断肝法”被写入《美国外科学院多媒体手术图谱》,成为迄今唯一被收录的中国原创技术。
“伤口还可以更小,突破的手术禁区可以更多!”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歇。腹腔镜肝切除技术成熟后,蔡秀军将目光投向了更险峻的“无人区”——为晚期肝癌患者谋求“一线生机”。
这些患者往往因肿瘤巨大、残余肝体积不足,被传统手术拒之门外。国际新兴的ALPPS技术(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分阶段肝切除术)虽带来希望,但术后胆漏率高达30.6%的难题制约着其应用。
深夜的办公室,蔡秀军常常对着肝脏模型陷入沉思。憋着一股钻研的劲儿,最终,他创新性地提出用特制弹力带“绕肝捆扎”替代传统肝脏离断。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背后是无数次动物实验和力学测算。
2014年,这项被国际肝外科界誉为“蔡氏ALPPS”的技术成功实施。《自然》杂志以“钥匙孔手术解锁肝移植新可能”为题进行专题报道,评价其“为严重肝硬化和肝癌患者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
在蔡秀军的带领下,浙大邵逸夫医院更早地拥抱微创外科发展的浪潮。如今,微创技术已在浙大邵逸夫医院外科领域遍地开花,微创手术占比超过80%,并延伸至内科。医院配备的两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更是创造了全球首例机器人单孔左半肝切除术的纪录——手术仅在患者腹部留下一个3厘米的小切口和一个1厘米的器械孔。
他反复地告诉每一名年轻医生:“微创不止于伤口小,更要体察患者的每一分不适。”
有一名肝癌术后病人,老说刀口痛。有些医生认为是病人娇气,手术后刀口哪有不痛的?蔡秀军在查房时听说了情况,他俯下身仔细观察,并触摸了手术切口,最后用撑开器轻轻撑开切口,得出结论:切口积液。经过对症治疗,病人的刀口疼痛消失了。
每天清晨查房时,蔡秀军总会细心查看患者腹部的伤口。那些越来越小的疤痕,见证着一位医者始终不变的初心。
追逐医学“潮流”,耕耘创新土壤
在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连廊里,有些特别的风景——
你会遇见刚下手术台的医生,白大褂还未换下,就带着热乎的临床数据奔赴实验室;工程师们熟门熟路地来到会议室,与主刀医生探讨器械的改良细节……
62岁的蔡秀军走在这里时,步履轻快。他总爱驻足观察往来的身影,“医生哪能被学科框住呢?医学一直在更新,医生,更要追逐医学的潮流”。
蔡秀军自己就是个不愿被框住的人。作为医工融合最早一批实践者,早在21世纪初,当多数外科医生还专注于精进手术技艺时,他就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2005年,他成功完成国内首例完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技术上的突破并未让他满足,反而让他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一针要缝五分钟,一场手术下来多出七八个小时。这样的微创还远远不够。”
这个困扰促使他开启了一场跨界探索。他从“壁虎断尾重生”自然现象中获得了灵感:人类的肠腔是否也可以自愈。于是,他主动联系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拎着病历和草图找上门去。“我需要一种材料,”他对材料学专家说,“既要支撑肠道愈合,又能在完成任务后自行降解。这可以实现吗?”
这个在医学领域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在交叉学科的碰撞中找到了可能。他们从仿生学原理出发,与工程师一起筛选了百余种高分子材料,逐一测试韧性、降解速度和生物相容性。历经数十次迭代,团队终于研发出可降解肠吻合支架,缓解无数肠道手术患者痛苦的“支架法肠吻合术”由此诞生。
后来,他带领团队在第一代支架基础上创新性增加可降解隔膜,研发出具有转流功能的“智能支架”,创立“支架法肠转流术”。这意味着患者从此可以免去临时造口的痛苦,也颠覆了全球沿用170年的德国“回肠造口术”。
医生的责任与使命,从来不只是在手术台上完成的。
在蔡秀军看来,随着医学技术不断更新,跨界的脚步不能停歇。但这不是跟风,而是始终围绕患者需求。
为了研发多功能手术刀,他和导师彭淑牖跑圆珠笔厂;患者术后肠腔过细,吃普通食物容易肠梗阻,他就联系营养科医生和食品加工厂,一起研发专属食品;发现手术机器人存在“力感知缺失”的世界性难题,他立刻联合浙大工科团队,研发出“Sliputure”活结智能缝线,使年轻医生的打结精度堪比高年资主任,稳定性高达95%……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闭门造车,得有人敢想,有人敢支持,有人敢试错。”他深知,创新更需要培育开放、包容的生态。
2016年、2017年,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主任范顺武先后带着两名爱徒——科研能力出众的硕士毕业生林贤丰、陈鹏飞,敲开了蔡秀军办公室的门。两人都想留在医院,却卡在了招聘的“硬件”条件——博士研究生上。
“老范,我相信你的眼光。”蔡秀军爽快拍板,“浙大邵逸夫医院是融合、开放、包容的医院,只要他们足够优秀,就应该不拘一格纳人才!”
这两名年轻人被破格录取后,很快投入到新型骨材料的研发中。他们想通过猪骨脱免疫组织技术,破解国内人骨来源紧缺的困境,却一度陷入转化的难题。
“我当时鼓足勇气给蔡院长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出现在实验室。”林贤丰回忆,蔡秀军鼓励他们继续自由探索,“你们知道吗,我们做的肠吻合支架,从想法到临床应用,整整用了16年。”他分享着自己的经历,“交叉的想法很好,这个东西要坚持下去。”
在寸土寸金的医院科研大楼里,他特批了一方宝贵的实验场地给这群敢于梦想的年轻人。在蔡秀军的支持下,团队最终成功研发出世界首款猪来源脱细胞脱矿骨基质产品,有望替代同种异体骨,应用于四肢非承重骨缺损的填充修复。
至今,蔡秀军都保持着这份对新事物、新潮流的敏锐与热情。平时,他总爱兴致勃勃地和年轻人交流:“嘿,现在流行的AR眼镜,”他会突然抛出问题,“在没有信号的地方怎么办?能不能开发移动信号站,用于远洋渔船、徒步探险等场景?”
在他耕耘的这片创新土壤上,也生长出一个又一个扎根临床的想法,最终结出惠及患者的果实——
截至2024年,浙大邵逸夫医院累计获发明专利近300项、实用新型专利近1500项,完成15项成果转化。医院国家基金项目和科研经费保持年均15%到20%的增长率。
“浙大邵逸夫医院是年轻的医院,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包袱,意味着可以勇敢闯、大胆试!”蔡秀军指着那条长长的成果转化连廊,“你看,它连起了什么?手术台与实验室、临床与产业、还有经验与未来。”
力行医疗改革,用创新破解看病难题
深夜的院长办公室,灯还亮着。
蔡秀军结束了一天的手术和会议,开始处理院长信箱里的来信。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表扬信我看得相对少,主要是找问题。”
昨天,一位患者反映,钱塘院区发热门诊排队时间太长。他立即协调科室增派人手,迅速缓解了排队压力。不久前,有员工注意到,6号楼门诊的扶梯走向让上下楼的患者在电梯口“碰头”。他请后勤部门现场调研3天后,果断调整了扶梯走向。甚至当有来信提到“医院某处冬天蚊子很多”时,他也认真对待,组织人员找到了管笼检修洞里的蚊子滋生地并彻底清理。
“这样做不是作秀,而是务实。”蔡秀军说,“听到来自基层的呼声,知道员工们在关心什么,患者们想表达什么,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同样体现在医院的建筑设计上。
在庆春院区五期大楼的设计阶段,蔡秀军提出了“平疫结合”的理念。他亲自参与设计,让普通病房通过隔离门和正负压装置的巧妙设置,能快速转换为标准的“传染病病房”。当发现新建连廊与4号楼存在高度差、影响推车通行时,他没有接受施工方“只能做楼梯”的说法,而是苦思数日,最终通过平移大门、加长坡度的创新方案解决了问题。
“涉及就医流程,医院容不得‘可改可不改’的事。”这句话成了他推进医院建设的准则。
浙大邵逸夫医院创造了许多全国首个:“门诊不输液”“病房不加床”“一人一诊室”等服务模式,从源头上提升了就医体验;“主诊医生负责制”“委员会制度”“入院准备中心”等管理创新,让医疗资源运转更高效。在蔡秀军的带领下,这些创新不断迭代,进一步从制度上确保了患者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医疗服务。
“文化不是一夜之间建立的,模式的转变也非一夜之间发生。”蔡秀军深知,真正的变革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蔡秀军为青年医生讲课。 受访者供图
作为年轻的医院,也是一片医疗改革的“试验田”,浙大邵逸夫医院肩负着更大的使命。
2013年开始,浙大邵逸夫医院分别与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江山市人民医院等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如今,借助远程手术机器人,医院专家不用远赴基层,就能实时指导当地医生开展复杂手术,让偏远地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让医疗普惠的种子扎根在基层土壤里。
2021年11月,浙大邵逸夫医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约共建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李哲勇医生是首批援疆团队成员之一。边疆的工作让他深刻理解了医者的家国使命:“当年阿拉尔需要帮助时,蔡院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什么条件都没提。他以身作则,每年都要来阿拉尔好几次,不仅指导医院工作,还深入团场卫生院,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从调整一台扶梯的走向,到构建辐射边疆的医疗网络;从解决一个蚊患问题,到设计“平疫结合”的战略布局——蔡秀军用行动诠释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深刻内涵。
“健康中国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医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蔡秀军说,“我们要用创新破解看病难题,用技术守护生命尊严,用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持续延伸优质医疗的边界。”
【链接】蔡秀军的仁心“智”造
腹腔镜多功能手术解剖器
该器械集剥离、电凝、切断、吸引、冲洗等多项功能于一体,术中不需要频繁更换器械,缩短了手术时间。同进口切肝器械超声刀等相比,对硬化肝脏具有切肝速度快的优势。创建了腹腔镜刮吸解剖法切肝技术,应用发明的器械逐一分离出深埋在肝实质内的管道,按其粗细分别予以电凝和钳夹处理,有效减少术中出血,该术式被编入美国外科学院多媒体手术教材。
可降解肠吻合支架
蔡秀军提出了实现“免缝合”肠吻合的理念,发明了可降解支架并创建了支架法肠吻合术,吻合时间短,避免了吻合口黏膜下血管的破坏及异物残留,有利于愈合,减少吻合口漏的发生。该发明实现了高效肠道吻合,腔镜下实施方便,并可用于治疗肠瘘、肠穿孔及战地肠损伤的一期修复,是肠道外科领域的重要突破。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9项及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国专利。
可降解肠转流支架
该支架由可降解高分子材料制成,用于“支架法肠转流术”,实现了“无造口”肠转流,替代由德国人发明的、已沿用了170年的回肠造口转流术。该技术与传统造口术相比,避免了肠造口、人工肛门留置及二次回纳手术,将治疗周期由3至6个月缩短至3周,大大减少了对患者生理、心理的创伤。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多项及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专利。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