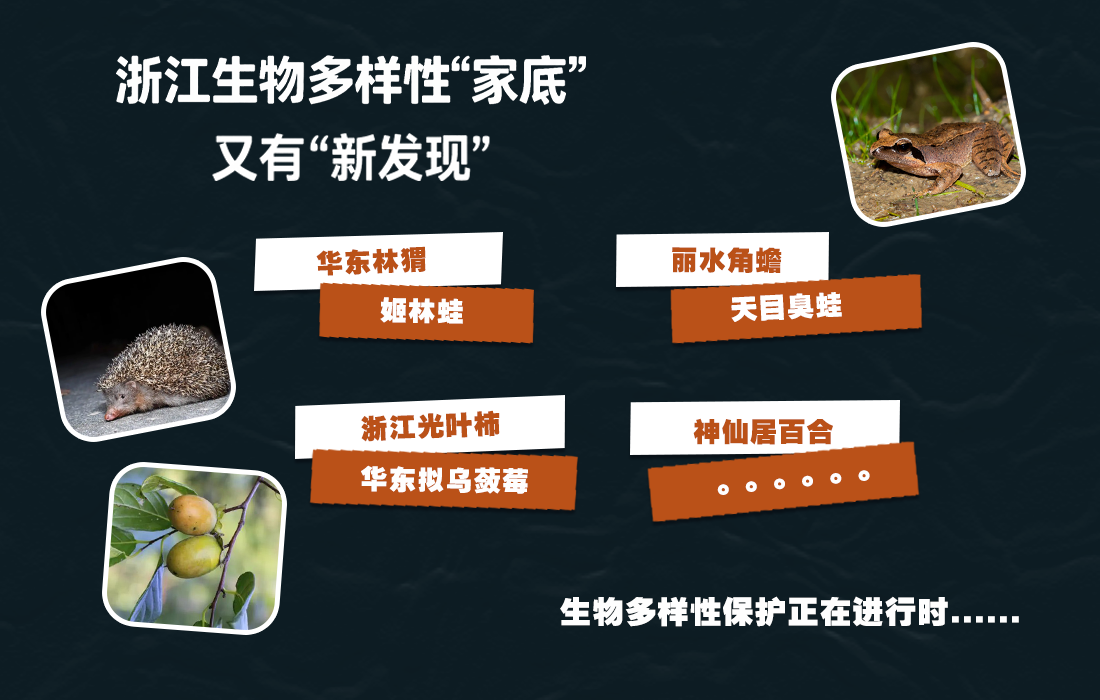李安宁拍摄的南宋“天封塔地宫殿”铭银殿。

李安宁拍摄河姆渡文物。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浙江在线11月20日讯(记者 陈醉 通讯员 项聪颖)微微倾斜的拍摄台上,宁波博物馆馆藏文物清代玉器“马上封侯玉带钩”,沐浴在柔和的仿自然光中。这件宝贝不久后将“出席”一场文物展览,文物摄影师李安宁正在为它拍摄“宣传照”。他单膝跪地,镜头贴近,指尖不断细微调节,准备在最佳状态时按下快门……
一脚迈进宁波博物馆文物摄影棚,我们便被眼前这几乎静滞的画面吸引了。我们弯下腰,试图透过镜头里的角度走进李安宁的世界。2008年,宁波博物馆落成开馆,随之而来的是对馆藏文物的系统梳理和数字化建档,需要细致地拍摄文物。两年后,原本是一家广告公司展览设计师兼摄影师的李安宁,受邀加盟筹建中的宁波博物馆文物摄影棚,将镜头对准了文物。
当前,全国备案博物馆有7046家,很多大型博物馆都有像李安宁一样的文物摄影师。
减轻光照影响,闪光灯加装特制涂层
清脆的一声“咔嚓”后,李安宁起身,端着相机翻看刚刚拍摄的“马上封侯玉带钩”,贝雷帽檐下的眼睛弯成了月牙:“这次拍摄完工。”
“每次按下快门,都像为千百年后的观众创作一篇详尽的解说词。”李安宁抬头看向我们,这位留着艺术家式小胡子的文物摄影师,用充满诗意的开场白,向我们敞开文物摄影的大门。
“等会儿我们还要见一位‘老朋友’。”李安宁略带神秘。不一会儿,他和助手从文物库房将一个“大家伙”运到摄影棚:“看,大名鼎鼎的南宋‘天封塔地宫殿’铭银殿,1982年出土于宁波天封塔地宫。”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单檐歇山顶银制建筑模型,顶部与主体各自沉睡在特制的木箱中。
“这个‘老朋友’跟15年前一样,没什么变化!”李安宁轻声嘟囔。原来,这件入选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的银殿,正是他进文物摄影棚时拍摄的第一批文物之一。最近,因为要将其现状上报国家文物局,需要重新拍摄。
我们在距木箱两米多远的地方架设三脚架。我们拿起补光灯试了试,光线并不强烈,可李安宁一再叮嘱:“光线不能太强,离远点!这也能避免碰到文物,文物安全第一。”李安宁补充道:“我们的设备都经过特殊处理,比如相机闪光灯加装了特制涂层,以减轻光照对文物的影响。”
“每次拍摄文物,我都当成最后一次,要小心翼翼护其周全,尽量少去打扰它们。”李安宁说。
展示文物细节,拍“写真”妙招连连
一切准备就绪,可“主角”躺在木箱里不能动。李安宁解释:这位“老朋友”将近900岁了,已经很脆弱,必须保护其安全,不能搬出木箱。我们非常纳闷,按常规,文物拍摄留档需各个角度拍摄,放在箱子里该如何操作?
没等我们回过神,李安宁已拿出一面镜子,晃了晃说:“难不住我们,就靠它来投影!”受到牙科医生启发,李安宁想到借用镜子从不同角度观察、拍摄文物。 “我们要脑洞大开!”
这面普通的镜子方方正正,边长大约20厘米。李安宁将其递给协助拍摄的文物修复师。修复师驾轻就熟,小心将镜子贴着木箱内壁缓缓放下,动作轻柔,避免触碰文物。当镜子被调整至合适的位置,藏在箱子里的文物细节就逐一显现在镜中。李安宁迅速捕捉影像,按下了快门。最终,李安宁为这个南宋“天封塔地宫殿”铭银殿拍摄了10余张高清图片。“可惜不能端出来,没能拍到文物底部。”李安宁略感遗憾。
怎样才算“脑洞大开”?在参观了李安宁的文物摄影棚后,我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9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是创意:用橡皮泥巧妙塑形,作为临时支架,支撑那些不便固定的文物;把圆柱形、容易滚动的器物放置在开有凹槽的亚克力装置上,稳当又便于观看……“文物要展现每一处细节,就要灵活运用各种器具,调整好角度与光线,让器物纹饰、锈色层次等在镜头下立体鲜活。”李安宁说。
摄影棚里的两台小型机床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机床边上堆叠着形态各异的奇特工具。“这些都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秘密武器!”李安宁满是自豪。
站在机床旁,我们拿起一个由细竹片与竹制方形底座组成的装置,李安宁称它为“扇骨支撑架”,竹片与支架巧妙咬合,可以精准地固定展开的古扇扇面,“用它,我拍摄了数百把古扇呢!”转而,他又指了指一堆小块塑料板,每块只有一把钥匙大小,用铝箔包裹着正反两面,“这是迷你反光板,我曾用它们为指甲盖大小的翡翠件打造出高光效果。”听着他细细讲解,我们愈发期待他拍摄的文物“写真”。
穿越时空,和清代扇骨创作者“对话”
在博物馆电脑的资料库里,存放着李安宁为7万多件文物拍的“写真”。
“这7万多件文物是2008年宁波博物馆落成开馆时的全部‘家当’,去年基本拍摄完毕。”李安宁说。这几年,博物馆陆续收入几千件文物,充实馆藏,目前,他正着手拍摄这些“新成员”。平时,他还需要为各种文物展览拍摄影像资料。
我们迫不及待地翻阅,一组清代浅雕松鼠扇骨的照片很快吸引了我们。
“第一眼看到这个扇骨时,我就被上面细腻的雕刻所吸引。”李安宁凑上前来,兴致勃勃地讲起拍摄这件文物时的场景。
拍摄之前,李安宁仔细观察,他发现,刀刻的角度会随着光影角度的变化而呈现不同效果。松鼠像活的一样,扇骨向前倾,眼睛闪闪发光;向左侧一点,毛发金光锃亮;把正,毛发舒展蓬松,尾巴变得又松又软;向右一侧,骨感筋道;向后一倒,露出爪子、呼之欲出……
“我把自己想象成执刀的工匠,一会儿在老屋的门口雕刻松鼠的筋骨,一会儿换个角度刻它的毛发,天暗下来时在微弱的烛光中雕刻松鼠的眼睛,使用不同的刀,刻、压、冲、划、勾、拉、拨、剔。”这种代入感,让李安宁在拍摄中不断变换灯的高低远近、光线强弱和角度。
“扇骨创作者当年创作时在飙刀技,如今我是在摄影棚飙‘光技’,我们穿越时空对话、接力。我累到腰直不起来,一共拍了72张不同效果的照片。”李安宁觉得,经历这样的过程,他与文物之间有了越来越深厚的情感。
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的李安宁,我们开始理解:优秀的文物摄影不仅是留下影像,更在于捕捉“魂”——以光影为载体,将文物的生命信息永久保存,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便利。李安宁举了一个例子,被誉为“宋画第一”的《溪山行旅图》,因为高清晰度的翻拍图片,得以放大研究,最终发现树叶间隐约现出“范宽”二字,因而确认了作者身份。
我们回味起初见李安宁时他的深情描述:“或许千百年后,人们会通过留存的影像凝视今天,会看到我们小心翼翼守护文物的痕迹。”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