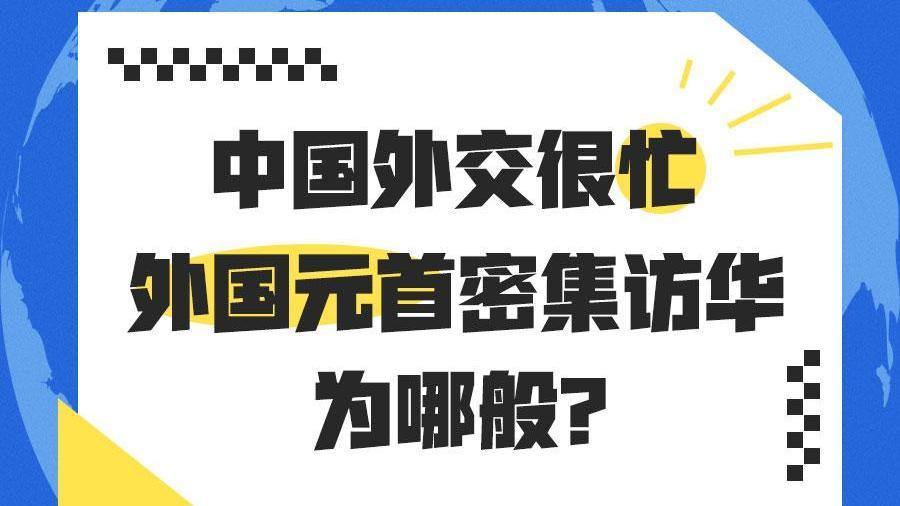“交流与共新: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主题特展正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出,跨越五千年、来自丝绸之路各个国家的210余件/套展出文物各有神采:它们在讲述丝绸之路上,物质的流通和商品贸易,怎样使得亚洲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交流与联系;这个共通的世界里,大家如何共享文明的成果;这些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共同拥有,又怎样让全球民众的价值观念、生活品质和物质条件逐渐趋向同一,从而使世界变成一体。
“丝绸之路”这个称呼,出现得比这条贸易之路晚了两千多年。直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在《中国》一书中正式提出,将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
这个名词经过各国历史学家、汉学家的沿用,特别是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著作《丝绸之路》,逐渐成为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贸易圈的代名词;甚至可以说,丝绸之路意味着数千年来人类古代文明的交流史。在今天,它仍然是世界史和全球史的最重要象征。
当然,穿过丝绸之路流动的,不仅是丝绸,还有香料,瓷器,皮毛和药材等千奇百怪的商品;通过丝绸之路的,除了商品,还有各类物种,以及运输、贩卖这些物品的人。大规模的流动人群,也带着他们的语言、信仰的宗教、经验和技术知识……连接起了这条路上的国家和文明。
2015年,英国学者彼得·弗兰克潘(Peter Frankopan)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展现了丝绸之路更广泛的面向,包括抽象的和具体的内容——这条路可以是信仰之路,基督之路,变革之路,天堂之路,铁蹄之路,重生之路,黄金之路,白银之路……
但尽管如此,彼得·弗兰克潘仍然为自己的书取了100多年前斯文·赫定用的书名,丝绸之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古代东西方文化大交流中,丝绸的重要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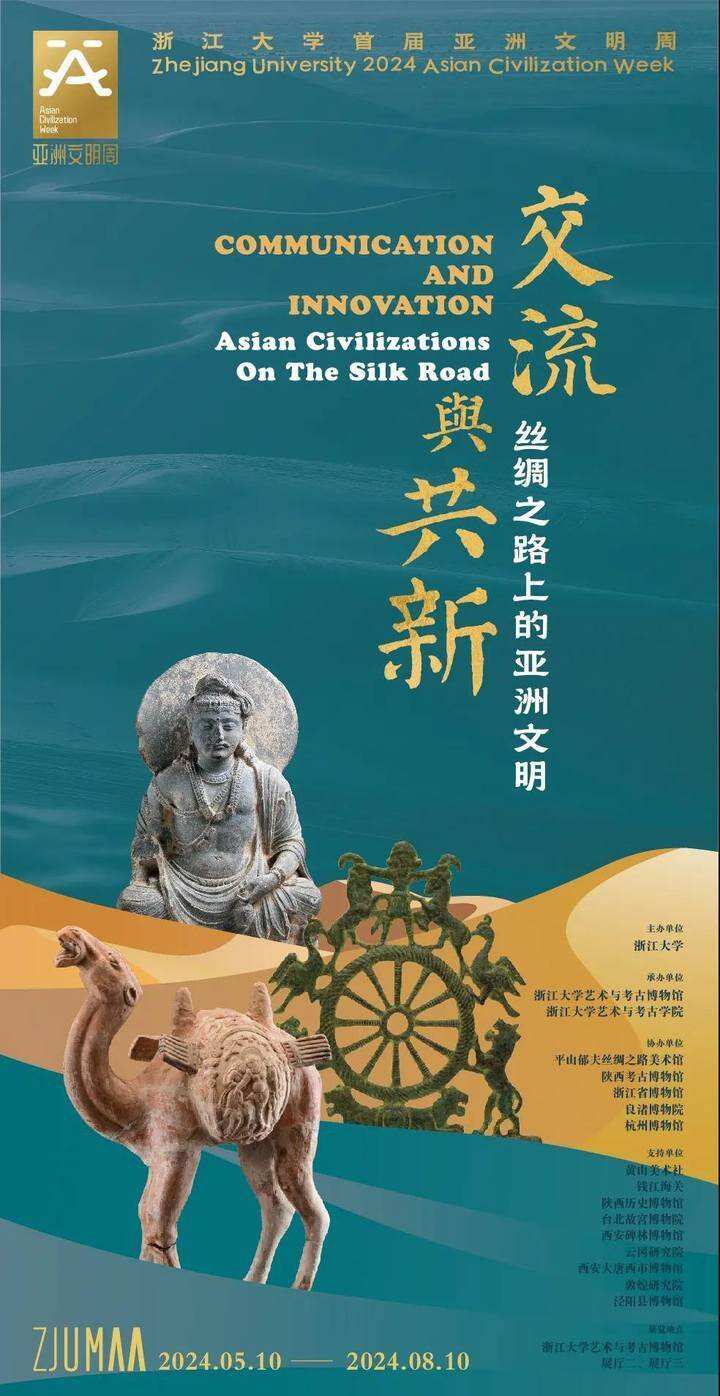
那么今天讲述亚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我们也从丝绸,这种风靡世界的物品说起。
“交流与共新: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主题特展总策展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赵丰,挑选了展出的三件唐代丝织物,作为引导观看的切口。
丝绸虽不像食物那样关系到生死存亡,但它们的故事却与中国人乃至亚洲大陆各族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呈现出来的,是众多的宗教、文学、艺术和民俗内涵。
一件罗:刺绣金孔雀
“交流与共新”·“器与艺:文明的延续与互鉴”展厅里,有一块四方形的织物,它的底是一件罗织物,罗的表面具有细密的纱空眼,质地轻薄、通风透凉。自1000多年前,它就一直藏在唐长安城西扶风法门寺塔的地宫中。
1987年,在一场大雨后,扶风县里的法门寺塔轰然倒塌了一半。今人由此见到了法门寺塔塔基下那座唐代建造的一座地宫,里面供奉着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公元7-9世纪,作为最高规格的皇家寺院,法门寺地宫中还藏有大量珍宝,包括数量众多的丝织品——其中属于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等皇室帝胄供奉的织物,就达700多件。
法门寺每30年开启一次地宫,佛骨被迎入宫中供养一番,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次在这个过程中,皇室会同时更新地宫中的供养品,尤其是其中的丝织物。
唐懿宗时期最后一次迎送佛骨后,法门寺地宫从公元874年封闭,到公元1987年倒塌后接受考古发掘,在漫长的1100多年时间里,这些晚唐的织物再没有经过人为扰动。
在“交流与共新”特展上,观众看到的这件法门寺出土的大红罗地刺绣夹袱,当时是用来包裹供养品的织物;展区另有两件带莲花纹的蹙金绣织物残片。

唐大红罗地刺绣夹袱 中国陕西宝鸡 陕西考古博物馆藏 朱炜佳/摄
丝绸的主要成分是有机物质蛋白质,它对环境干湿变化极其敏感,因此丝绸织物在关中和中原地区通常很难保存下来。当今能够在展览中看到法门寺地宫的丝绸,非常难得。
大红罗地刺绣夹袱,尺寸和手绢相当。
它的图案非常精美,红色罗地上刺绣的主角是孔雀:正中间有一对呈现太极形循环的孔雀,它们相互盘旋、对称,寓意喜相逢。
夹袱的四角分别绣有四只造型不同、首尾呼应的孔雀,它们之间有四只蝴蝶穿插。
孔雀的母题,早先可能在印度产生,后来也多见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孔雀作为装饰语言在中国出现,则与亚洲国家的地域交流有密切的关联。

唐大红罗地刺绣夹袱刺绣图案复原图
更难得的是,这是金孔雀。这块织物的刺绣工艺,采用了蹙金绣。
蹙金绣缝的不是普通丝线,而是捻金线或者捻银线。比如这件蹙金夹袱中,孔雀、蝴蝶的主要部位,都是在丝线上绕着金线进行刺绣而成。
用金线织绣的方式,与东西方交流有密切关系。此前,中国的丝织工艺用金不多,在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了中西这条商贸大道之后,大量黄金装饰开始出现。
蹙金工艺从唐代开始流行,当时做捻金线,没有复杂的机械,靠的是匠人纯手工。以捻金线作为装饰,正是法门寺丝绸织造技术和装饰技法的一大特色。塔基地宫出土纺织品,代表了唐代纺织工艺的最高水平,尤其是用金工艺,对后世的织造、艺术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件锦:团花与翼马
西域对东方丝绸的狂热爱好,推动了养蚕和丝织技术的西渐。不少国家和地区掌握了丝绸的奥秘以后,结合自身的文化,开发出独特的织造技术和纹样,有些甚至反哺到丝绸的故乡,中国。
锦,是一种用彩色经纬丝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复杂布料,摸起来手感比较厚,生产工艺要求高,织造难度大,是古代最贵重的丝织物。
锦的织造工艺分为经锦和纬锦:经锦是中国传统织造技术,以经线显花,在战国时兴盛,两汉时期达到极高水平,并在公元前后传到地中海沿岸。较早对中国经锦加以创新改造的,是地处东西贸易轴心的波斯萨珊王朝,改造后的品种称为纬锦,它是西亚结合中国丝织技术与当地毛织技术,以纬线起花、斜纹组织形成的工艺,图案更加丰富。后来这种技术又传入中国,在盛唐时期取代经锦,成为主要品种。
在此次“交流与共新”特展中,有一块红地天马纹纬锦,是典型的粟特织锦中的翼马纹锦:大地色系织物上的马,低着头,它们长有翅膀,翼尖卷曲朝前,身上装饰繁琐,颈后饰有飞扬的绶带,腿部关节系缚绸带。这种饮水马或是食草马的织锦,有时会在联珠团窠环中出现,有时则会在织物上横向对称排列。

红地天马纹纬锦(局部) AD700-AD900 中亚 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朱炜佳/摄
翼马是丝绸之路上十分流行的题材。这种有翅膀的马,根源于希腊神话中飞马座珀伽索斯(Pegasus),它的主人珀尔修斯(Perseus),曾经骑着飞马前往斩杀蛇发女怪魔美杜莎(Medusa)。在传播至西亚和中亚的过程中,形成了萨珊波斯风格的翼马纹样。
这类织物在丝绸之路上广泛传播:从地中海边到中亚粟特再到中国的西北地区,都曾发现过属于波斯和粟特系统的翼马纹纬锦实物。
在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北朝晚期至盛唐的织锦中,经常可见翼马的形象,其原型就是珀伽索斯。
展厅里,这群翼马的隔壁,有一朵巨大的团花。这也是一件斜纹纬锦,但却是典型的中原织物。这件团花纹织锦虽已是局部,但可见原件极宽的门幅:左边能看到幅边,纬线方向大约横跨了近1米,仍不见另一条幅边。就在现有的这么大面积的织物上,差不多就开了一朵团花。

唐黄地团窠宝花纹纬锦(局部) AD800-AD900 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 朱炜佳/摄
唐代典型的团花图案,源自汉晋时期常见的柿蒂花,后来越开越大,图案的风格越来越复杂。在唐代的许多装饰中,都经常可以看到团花纹,比如敦煌莫高窟唐代洞窟中的藻井,唐代的金银瓷器、方砖上,都有团花纹样。
这朵团花已属于华丽的宝花纹样,由三层花环组成:含苞欲放的花朵,花蕾,盛开的花瓣和花叶层层叠压,叶中有花,花中有叶。
其中第二层团窠织有花的枝蔓穿插着花朵中,整个构图因此立体灵动起来,“相比团花特有的造型,这是很写实的表现方法,宝花显得更加清秀,这是到盛唐以后才有的风格。”
赵丰说,团花尺寸大,也意味着织造技术复杂。西域的织物图案,往往左右循环对称,上下不循环,比如上述的天马。而中国的织物,左右上下都循环,“说明新的提花机在中国境内出现了。”赵丰粗粗一数,这朵蓝绿黄色系的团花,至少包含了6-7种颜色,“也就是说,每织一道纬线,需要投6、7把梭子才能完成,非常费工。”
目前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一件大团花图案织物,是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蓝地大窠宝花锦琵琶袋。

蓝地大窠宝花锦琵琶袋 日本奈良正仓院藏
一件绫:方寸见乾坤
“城与人:文明的交汇与创新”板块,古城平安京的展厅里,最后的展区有几块尺幅非常小的织物残件,是一组奈良时期(传)藏于日本法隆寺的藏品。

赤地格子莲花纹蜀江锦 AD600-AD700 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 朱炜佳/摄
一块红地格子莲花纹蜀江锦,是其中色彩最跳的一件展品:这件经锦上的方格纹样,以及每组方格里包含的小的联珠团花图案,都与隋到唐早期的织物风格一致。在中国青海都兰地区曾经出土的丝织物,敦煌壁画上的隋代人物服饰,以及唐墓中彩绘俑的服饰,都发现了类似的几何纹样图案。这类织物在日本都被称为蜀江锦,也就是说,日本人都认为它们是自中国成都地区输入了,应该就是蜀锦。
而蜀江锦旁边小小的一块织物,只有掌心大小,看上去平平无奇。如果不站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观众甚至完全会错过这块乳白色残绢上,织有十分精致的暗纹:正是在唐代盛行的联珠团窠纹,方寸之间还可见连接团窠的宾花纹样。但由于实物尺幅太小,很难判断团窠中间的纹样是动物、人物还是花卉。

传法隆寺绫(残) AD600-AD700 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 朱炜佳/摄
“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都是中国生产的织物,并且很有可能也是来自蜀地。”赵丰谈起另一块与这件织物差不多时代的出土文物:
1959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21号墓中出土了一块“联珠团窠龙纹绫”,它的背面有墨笔行书题记:“双流县,景云元年折调紬(细)绫一匹。”在唐代睿宗景云年间,双流即为蜀锦的产地。
“(浙大展厅里)这两件织物明确代表了中日丝绸文化,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实证。当年,这些织物经由遣唐使带回,最终在日本保存至今。”
日本政府在唐朝近三百年间共派遣出遣唐使13次,唐政府亦回访6次,每次人数在一、二百至五、六百不等。遣唐使来时带有大量的供物,主要有各种絁(shī 一种粗绸)、绵、彩帛。唐朝廷回赠得更是慷慨大方,如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遣唐使入长安者赐绢1350匹。
每次遣唐使返回日本,日本皇室总是将唐之答信物供起,然后将唐之彩帛颁赐亲王以下参议以上及其内侍,有些还设市转卖,可知道数量之巨。
日本的正仓院、法隆寺至今藏有大量唐代丝织产品,其中的蜀江锦、大窠双联珠对龙纹绫、四骑狩狮锦等,都明显带有中国舶来品的标志。
三块丝织物的故事讲完了,它们只是浙江大学“交流与共新:丝绸之路上的东亚文明”特展的小小一个索引。这次展览总共展出的210件(套)各种类型文物,它们代表了丝绸之路上的一种文化交流精神:不只是对自己身份与文化价值的肯定,更多的是对他者的迈进,关注文明之间的互鉴与融合,向外界拓展出更加广阔的世界。
各位可以在今天(5月18日)潮新闻推出的直播导览中,看到策展团队关于此次展览中近20件重磅文物的介绍(前往观看)。当然更欢迎大家前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亲历观看,数百件几经沧桑的文物,它们一定在朝你呼喊:“还有我,还有我!”
(关于交流与共新: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览,潮新闻将邀请更多专家,解读更多类型的文物故事,敬请持续关注)

展讯
交流与共新: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
展览时间
2024年5月10日-8月10日
每周二至周日9:00至17:00
16:3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展览地点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厅二、展厅三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