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鲜明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
作为科技创新的底座,基础研究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当前,浙江正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提出,要在建设创新浙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重大突破。
有人说,基础研究是“无用之用”。那么,“无用之用”指的是什么?国家为何如此重视基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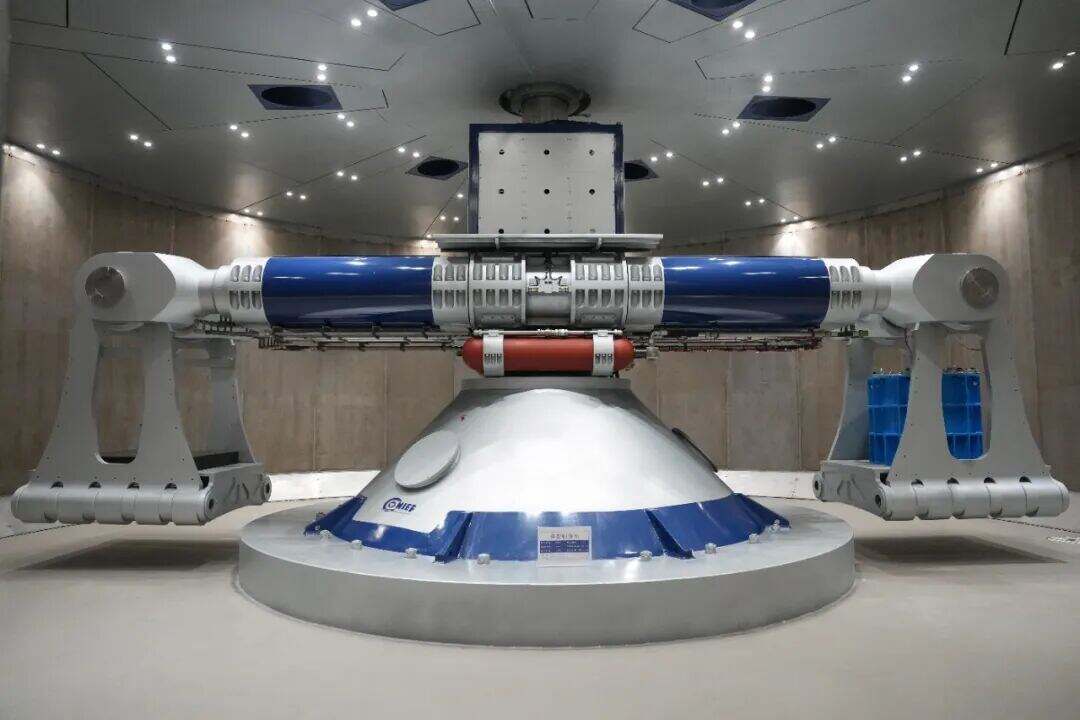
一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曾这么界定基础研究——
以深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等为基本使命,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培育创新人才的摇篮,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通俗来说,基础研究就是去挖问题的“根”,它不直接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带着好奇心去探索“是什么”和“为什么”。就像我们玩积木,手里的积木就是已知的自然现象,而基础研究,是发现新积木,弄懂积木的特性和规律。也许,今天我们不知道新积木能用来搭什么,但这会决定未来我们能搭建出怎样的世界。
基础研究之所以被称为“无用之用”,是因为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不确定性高,有“九死一生”的风险。可一旦突破,往往能引发科技创新的连锁反应,推动原创性技术革新,带来颠覆性技术革命。
比如,痴迷电磁现象的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后来,麦克斯韦用一组方程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而直到赫兹在实验室里捕捉到了电磁波微弱的电火花,人类才第一次“看见”了电磁波。当时有人问他,这项研究有何用途?赫兹的回答也很实诚:“毫无用处……这只是个证明麦克斯韦大师是正确的实验。”而正是这束“没什么用”的电火花,后来一路改写了人类通信史,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实用性:从无线电报到广播、电视,乃至如今的手机信号、Wi-Fi、蓝牙等,都与电磁波密切相关。
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所说,如果没有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不会有后来的原子结构、分子物理、核能、激光、半导体、超导体、超级计算机等一切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些“地基型”发现,一开始离现实很远,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10年时间、10亿美金、10%成功率”,这是医药界关于研发新药的“三个10”定律,既道出了创新的艰辛,更揭示了“厚积薄发”的创新规律。再看宇树科技、DeepSeek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的逆袭爽剧,而是数年如一日的“死磕”成就了创新。
由此可见,从发现到应用,基础研究的试错、探索向来不是以“日”“次”来计算的,而是需要十足耐心的漫长马拉松。

二
长期以来,中国科技以“应用优先”加速跑,可跑得越快,越感受到基础研究的“地基”深度决定着未来科技大厦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那么,究竟是什么卡住了基础研究?
“有用”的短视扼杀“无用”的远见。有人总习惯问:“这有什么用?”回头去看,科技的进步可能就源自当初看似“无用”的研究。屠呦呦在研制青蒿素的过程中,经历了190次失败,当时谁能想到它能拯救数百万生命?在烽火连天的年代,罗登义在煤油灯下钻研刺梨的营养成分,彼时鲜少有人能理解这项研究的意义。但这项“冷门”研究却在几十年后让贵州打造出刺梨产业,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基础研究既是技术创新的“米”,也是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源代码”,正如任正非所说:“如果不搞基础研究,就没根。即使叶茂,欣欣向荣,风一吹就会倒的。”
“跟跑”的惯性消磨“开创”的勇气。在长跑中,跟跑往往比较省力,在基础研究中,我们也会不自觉陷入跟跑的惯性。但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没有“从0到1”的原始创新就跨不过“卡脖子”这道坎。被称为“科研疯子”的黄大年,勇闯“无人区”,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推动多个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曾经令钱学森“久久不能平静”的问题至今仍发人深省,科技要大创新,就不能迷信“外国的月亮更圆”。
“功利”的观念侵蚀“纯粹”的好奇。人类的知识版图需要拓荒者,这背后靠的是好奇心,甚至是一点英雄主义驱动。华为每年投入大概600亿用于基础理论研究且不考核,正是认识到“没有理论就没有突破”。杨振宁曾说:“科学中存在着美,所有的科学家都有这种感受。”他一生所做的,就是靠近这种美。这种“感受”本身,就是意义。科研本应是用“睁大眼睛、充满求知欲”的好奇状态去探索世界,但一些科研人员却被困在“发论文、争项目、评帽子”的循环里,功利心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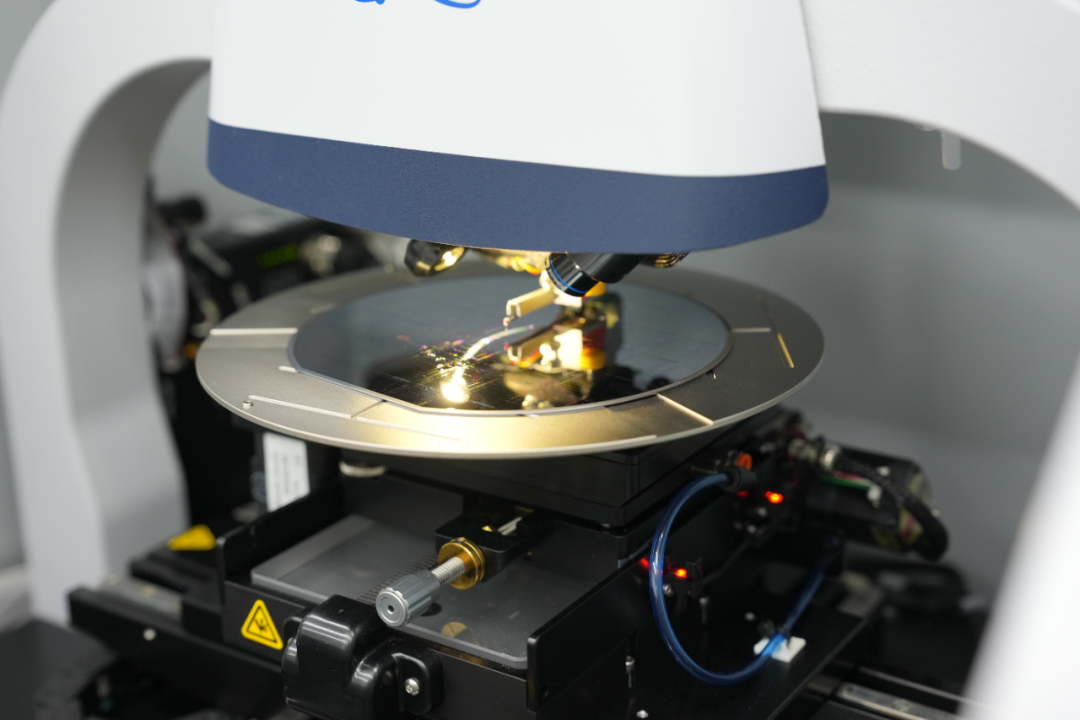
三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谈到,中国的基础研究正在“升温”。此类观察如同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智慧,如何转为走好下一程的势能?
让“评价时钟”走得慢一些。有些基础研究可能需要几代人的耐心,所以它的价值无法用论文数量去衡量。上海试水“基础研究特区”“基础研究先行区”,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给足资源、放开手脚。杭州之所以能孕育出活跃的“六小龙”创新生态,背后站着的是一个耐心政府,以长期主义的心态发展科技。说到底,能让科研人员坐住坐稳“冷板凳”,需要长周期的眼光、多维度的评价,为自由探索与大胆创新提供生长的土壤。
为“异想天开”留一片原野。阿基米德洗澡时灵光一闪发现浮力定律,伦琴实验室“偶然一瞥”发现X射线……科学史上许多重大发现,往往来自一瞬间的灵感迸发。这些瞬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既无经验可循,也无法预设,因此,基础研究尤其需要包容和自由。黄大年的“造梦空间”,华为的“黄大年茶思屋”,都是为鼓励自由交流和思想碰撞而设立。我国一直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就是为灵感留白,让思想呼吸,让创新走得更远。
让掌声为长期主义者响起。科技创新,犹如一场与未知对弈的拼图游戏。每一个“此路不通”的标识,都在为最终的抵达积蓄经验和力量。对于那些研究方向尚不明晰、方法理论尚未成型、失败风险较高的基础研究领域,理应给予更多包容,建立完善允许试错、奖励探索的评估体系,以“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的远见和“请再试一次”的鼓励,让敢于尝试的人无所顾虑,让敢于探索的人埋头赶路。
当前全球竞争进入创新“无人区”,我们既要沉下心来做原始创新,也要紧盯科技最前沿抢占制高点。在“十五五”新征程上,用“无用之用”撑起科技的筋骨,真正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稳稳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程!
版权和免责申明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







